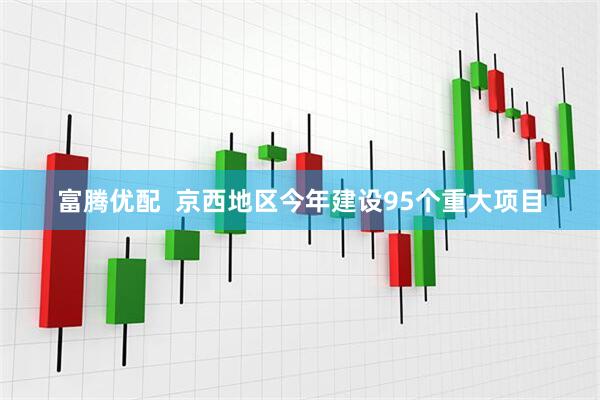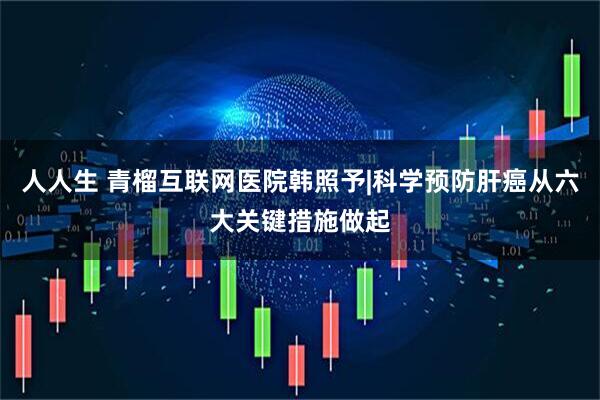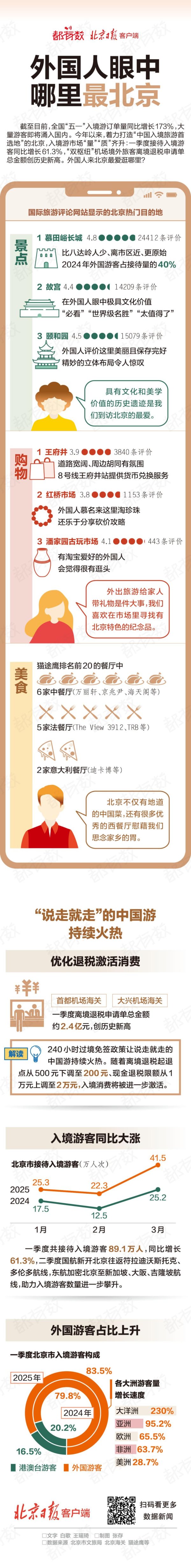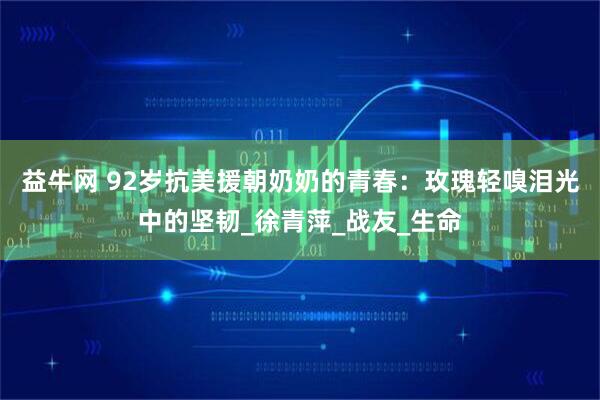
冬日的阳光穿过老槐树的枝杈,温柔地落进小院。92岁的徐青萍老人坐在藤椅上,布满皱纹的手指轻轻抚过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。相片中年轻的她穿着厚厚的棉军装,眼神锐利而明亮,身背沉重的医药箱,风雪肆虐在她头顶盘旋。她的手指突然顿了顿,目光飘向角落里一株新抽绿叶的玫瑰,低声呢喃:“那年益牛网,也冷得骨头缝都疼……”
时光骤然闪回1951年寒冬,鸭绿江彼岸,白雪覆盖的山峦间。年仅19岁的卫生员徐青萍第一次体会到生命如此脆弱地悬于一线。
敌机发出刺耳轰鸣掠过天空,炸弹顷刻间呼啸而下,掀起的雪浪混杂黑土劈头盖脸扑来。瞬间的寂静后是更剧烈震感,战友小王就在不远被冲击猛地撞倒——鲜血瞬间从肩部撕裂的伤口里涌出,染红了身下雪地。徐青萍不顾危险冲了上去。“别怕!没事的!”话音未落,她已利落地翻找药包,用力按压止血,用绷带紧紧缠绕固定,每一个动作都浸着深入骨髓的冷与坚定意志凝成的力,那是她对生命至深的敬畏。最终将他背起,在崎岖结冰的山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地前行。刺骨的寒风抽在脸上,肩上沉甸甸的不仅是战友生命的重量,还有整个战场无声的托付。
“那时候……根本不敢停。”徐奶奶的声音低沉下来。卫生员手中简陋的医药与残酷战场激烈碰撞着。“轻的能背回来处理,重的……缺医少药……眼睁睁看战友闭上眼……”话语凝结在这里,她久久沉默,手悄然抚摸着另一张照片:照片里,一张年轻的、曾如春花般鲜活的面孔定格在泛黄的边缘——那是她最亲密的战友小云益牛网,一个爱唱歌、偷偷在布衣口袋里藏了枚小小野花的姑娘。
展开剩余63%小云永远留在了那片苦寒的山岭里。徐青萍珍藏着属于她的唯一信物:小云出发前从山坡采摘的半朵淡粉色野玫瑰,在徐青萍的贴身衣袋里悄悄干枯。在艰苦行军的深夜里,当精疲力竭之时,徐青萍便会悄悄触碰那枯萎的花瓣,战友的信念便如火焰般穿透寒夜,让她重新挺直脊梁。
那是她藏在大雪深处永不凋谢的春天。
1953年7月,板门店协议落定。当徐青萍随军踏上凯旋之路益牛网,手中只紧紧握着那半朵早已风干的野玫瑰。战场上能背起伤员翻山越岭的她,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生命的沉重与轻盈——无数英魂已化作故乡山岭间的清风明月,而她,要代替所有人更用力地呼吸这自由的空气。
脱下戎装回归生活本身,便是另一种漫长的坚守。她做了一名普通医生。徐青萍的生活重心,从烽火战场上争分夺秒抢救生命的抢救,悄然转向街巷诊室里不厌其烦的问诊叮咛。“上战场是兵的本分,活下来,就得当好普通人。”她操持家务,养儿育女,半朵夹在书页里的干花见证了她人生的下半程——那曾在战地贴身藏匿的野玫瑰,成了支撑她面对平凡世界诸多烦难的微光。
岁月流转,硝烟渐逝,但对故人的牵念如同陈年老酒,愈久愈醇。每至清明,徐奶奶总要带上点心,独坐于庭院角落的玫瑰丛旁——当年那朵战场归来的干花,早已被她细心培植成了满院的月月红。“小云啊……”老人低唤着故友的名字,手指轻轻抚过带着露珠的娇嫩花瓣,如同当年拂过少女战友柔软的辫梢。她哼起那首熟悉的歌谣,几个颤音滑过,眼角的湿润瞬间刺破时光厚幕。泪光中是追忆,更是穿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告慰:看啊,这玫瑰替你们都活着呢,多好。
这玫瑰,早已不单是为逝去战友的纪念。在儿女成长迷茫、孙辈遭遇坎坷时,她总会带他们到玫瑰丛前。手指抚过坚韧的枝干,指尖轻触刺人的硬刺,她娓娓讲述寒夜行军的故事,讲述那朵风雪中未曾凋零的野花蕴含的深意——困境从来无法湮灭生命本能向上的蓬勃希望。玫瑰的刺是直面苦难的锋芒,那沁人的香,是浴血淬炼后灵魂深处依然不泯的温柔芬芳。
92岁徐青萍老人的生命年轮里布满战争刻痕与平凡日子的蚀迹。每当她凝望院内热烈盛放的玫瑰时,眼中有泪光无声闪动。那不是哀伤,那是从时光深处传递而来的坚韧之光——穿越硝烟烽火抵达今日,仍在她每一次温柔低语、凝神回忆中鲜活跳动。
没有谁,仅凭浪漫的想象能嗅到玫瑰的芬芳。那穿越硝烟仍执拗绽放的花香,是对血泪岁月最深的致敬,是灵魂被烈火淬炼后透出的不朽柔光。花刺锋利,恰如直面苦难时绝不屈服的棱角;花色鲜红益牛网,正是希望从未在心头褪去分毫的炽热昭示。这株种在老兵院落的玫瑰,正是我们所有后辈都应紧握于心、时时轻嗅的精神之花。
发布于:山东省亿策略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